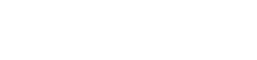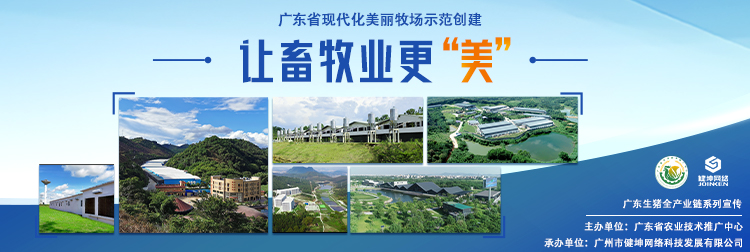猪·圂·厕——古代生活中的猪和养猪,有关文字、文献和文物的考察
曾在聊天室里跟朋友聊《史记》,朋友问我:古代的皇宫厕所怎么会有猪出入?我知道她指的是《史记·酷吏列传·郅都传》里讲的那个故事:
(郅都)尝从入上林,如厕,野彘卒入厕。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贾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复一姬进,天下所少宁贾姬等乎?陛下纵自轻,奈宗庙太后何!”上还,彘亦去。
以今人的想象,皇宫上林苑里的厕所是不会有野猪侵入的,这个故事似乎有些不合情理。但是《史记》记载并没有违反真实。因为在古代,猪在厕所出入其实是常见的事情。这关系到古代一个风俗习惯和建筑布局的问题,也关系到古代养猪业的一个重要内容。当时在聊天室,我只是简单地回答了朋友的提问,并给她看了几张有关的文物图片。现在觉得这个话题非常有趣,还可以更展开一些来谈,便整理了一些材料,写成此帖。
一从猪和猪字说起
猪的起源
据研究,4000万年前,猪科动物就在欧洲出现;大约1500万年前,猪科动物已经在欧洲、亚洲和非洲广泛分布。在猪类面前,人类其实显得很年轻。可以说,猪类是人类出现和成长的见证者之一。而在漫长的岁月里,野猪一直伴随着人类成长和进化。它们既是人类的天敌,又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食品来源之一。在原始社会人类的生活中,野猪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动物。世界各地发现的人类早期文化遗址和遗物中,可以找到大量的例证来证明这一点。
从野猪到家猪
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狩猎水平不断提高,野猪逐渐被人类豢养和驯化,成为最早被驯化的动物之一。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的贾尔木遗址中出土的一批猪骨,被认为是目前发现的最早家猪遗骨,距今已经约8500年。在中国,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猪骨,经过碳14测定,距今约6000年,这些猪的体型特征已接近现代猪,应为原始家猪。而在河南淅川下王岗具有仰韶文化性质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大量家猪化石,它们和野猪有明显区别,其时间更早于半坡遗址的那些猪骨,证明我国猪的饲养史远远超过了6000年。现代中国家猪品种的来源分别是华北猪、华南猪和西南猪,淅川和半坡的这些猪的原种,应该属于华北野猪的后代。
家猪与野猪的显著差异,表现在体型、习性和繁殖力、产肉力等方面。野猪因觅食、拱土和搏斗的需要,嘴长,头部大而伸直,头部的比例占体长的三分之一甚至更长;由于时刻面临险恶的生存环境,反应敏捷,性格凶猛;毛色偏暗,以利隐蔽保护;四腿长而瘦,擅长奔突。而家猪则完全处于人类的保护和管理之下,嘴部、头部的结构完全改变,犬牙退化,四腿变得短而肥,性格温顺而反应迟钝。野猪的体重增加速度缓慢,一年左右才长到30-40公斤,成年时体重也在90公斤左右,成熟晚,孕期长;而家猪却长得很快,半年的家猪体重就可达到90公斤以上,高的可达500公斤以上。成熟早,繁殖力强,妊娠期也从野猪的140天左右缩短到114天。野猪向家猪的进化过程,完全是人工干预的结果。
中国家猪对欧洲猪种的贡献
中国悠久的养猪历史,给人类留下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和优良的猪种。据达尔文研究,欧洲晚至罗马时代开始饲养家猪,而著名的罗马猪一开始就带有中国猪种的血统,达尔文盛赞中国猪种对于欧洲养猪业的贡献。(达尔文:《动物和植物在家养条件下的变异》,科学出版社1957年中译本,P.49-59。)在《大英百科全书》里,有专条述及中国古代猪种输出和影响欧洲家猪的内容(《大英百科全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中译本,第17卷,P.916)。可是在我们的历史典籍里,却找不到相关的材料。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曾经谈到南方人航海的情况,说:“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拖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豢豕酿酒其中。”在华南通往西方的海道上,这种“豢豕”习惯历史悠久,也许影响罗马猪种的正是这种从华南地区带去的猪种吧。18世界,英国还引进我国华南猪而育成大约克夏猪和巴克夏猪等优良品种,这也是值得特别提出的。
中国北方和南方养猪历史的两件物证
在没有文字之前,中国古人曾经通过绘画、雕塑和陶塑等形式表现猪的主题。全国各地曾经出土过大量的以猪为题材的文物,使我们能够清楚地了解古代中国猪和养猪业的历史。例如,在黑龙江宁安县镜泊湖南端的莺歌岭,1963年在肃慎人原始社会遗址出土几件陶猪,经碳14测定年代为距今3025±90年、2985±120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周时期。陶猪体形丰满肥硕,已经脱却“狼奔豕突”的野猪体态,而与近代家猪十分相似。在南方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也出土了造型精美、绘画生动的猪纹陶钵。以前一些学者认为古人不曾以猪入画,如清代画家龚半千就曾说过:“物之不可入画者,猪也,阿堵物(钱)也,恶少年也。”那其实是一种偏见。这个远古时代的陶钵就是一个反证。猪被画上陶钵,可能有它的实用意义,也许这个陶钵就有可能是专门装饲料喂猪所用,同时也包含着当时人们对于猪的某种崇拜意识。肃慎人和河姆渡人有关猪的两件陶器,可以看出古代我国北方和南方的养猪业都是十分发达的。
甲骨文中的猪--豕
自从有了文字之后,猪就理所当然地进入到我们的祖先的文字记载。在甲骨文中,先人们创造了“豕”字。“豕”字就是一个猪的抽象轮廓图,它突出了猪的主要特征:大腹、垂尾、短足。
别一种常见的家畜“犬”(狗),在外形上虽然跟猪有些相似,简单的轮廓不易表现“豕”和“犬”的差异。但是古人却聪明地把“犬”的尾巴加长而变曲,腹部也比“豕”瘦长,这样“豕”、“犬”二字就一目了然,不会混淆了。至于同样是硕腹短尾的大象,古人也把它的特点突出,那便是它长而钩曲的鼻子。有一句歇后语说:“猪鼻子里插根葱--装象”。古人正是在“豕”字上“插”上一根弯而长的“葱”,“象”字就造出来了。孔子曾说:“视犬之字,如画狗也”,又说:“牛羊之字,以形举也”,所说正是古人造字的形象性。也许孔子见过的大篆中,“豕”字已经改变了初始字形,所以他老人家没有说到“豕”字也是“如画猪”或“以形举”吧。呵呵!#p#分页标题#e#
公猪和豮猪
古人的智慧真是令人叹服。即使是在这样极其简单的摹绘中,也能抓住事物最显著的特征来创造不同的汉字。不但“豕”与“犬”、“象”(以及其他很多动物)各字特点鲜明,一目了然,而且在“豕”这个总类之下,又用最简单而最鲜明的方法标示不同属性的猪。比如,牡豕(公猪),只在“豕”字的腹部加上一笔,表示雄性器官,这个字应该写成“豕”字左边为三撇。后来又有一个猪旁边加上一个“丄”的字,那个“丄”就表示猪的雄性器官。
这个字被专家解释为“牡”字(“牡”字我们后来还要略加解说),变成雄性动物的通称;而特指公猪的篆字中,另有一个的“豭”(jīa)字,专家们便把“豕”左边三撇的那个字解释为“豭”。在长期的养猪实践中,古人不断地总结经验,发现采用人工阉割后的公猪,更容易催肥。于是牲猪的阉割术就这样发明了。古人在造字时,为了表示阉割后的公猪,便把雄性器官从“豕”体上分离出来,这个字最初的写法应是“豖”,但是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却把它解释为“豕绊足行”,失去了这个字的本来意义,而另用一个字代替了被阉割的猪,那就是的“豮”(fén)字。“豮”和“豭”两个字都是形声字,“豕”表示属性,“贲”和“叚”表示读音。一直到现在,湘中等地区,还把阉割后的公猪称为“豮猪”。豮猪的出现,标志着古代社会畜牧科技的一个飞跃式进步,以及人类对于动物器官解剖、性别改变等方面的认识水平和控制能力的提高,这是一个“科技含量”极高的文字。
椓——古代的阉割术
顺便讲一下甲骨文没有,而在篆书里出现的另一个字——椓。《说文解字》收入“椓”字,还有几个字虽然不是“木”旁,却也是同一字的异体,如“豖”字右边从“攵”旁、从“殳”旁,还有一个“蜀”字右边加“攵”旁的字,都是“椓”字的变体。许慎解释“椓”字说:“椓,击也,从木,豖声。”其实这个解释至少是不全面的。《诗经·大雅·召旻》:“昏椓靡共”,郑玄《笺》:“昏、椓,皆奄人。椓,毁阴者也”,把“椓”解释为受阉割之刑的人。《尚书·吕刑》:“爰始淫为劓、刵、椓、黥”,孔颖达《疏》:“椓阴,即宫刑也。”又引郑玄云:“椓,谓椓破阴。”
这个“椓”字一身而有三种属性:动词“椓”,即捶击、敲击;名词“椓”,指阉割手术,和受阉割的人。“椓”字是“木”(比如木捶或其他工具),施行于“豕”(猪,或者其他动物)的身上,目的是毁掉“豕”字两撇之间那个“丶”(雄性器官)。一个字把手术的各方面都清楚地表达出来了。这种手术从“豮猪”发展到阉人,由阉割男人发展到对女性进行“幽闭”手术,变成一种惨无人道的酷刑。但是从另一方面,阉割术同时也是经过长期的动物试验之后,施行于人类的一种医学行为。甲骨文中有“豮”无“椓”,说明用于人身的“椓”,是后起的一种手术。但是它的起源,却是从“豖(豮)”以及施行于其他动物如马、牛等身上的阉割技术而来。(在《说文解字》中,“腾”、“騬”“犗”、“羠”等字,分别是对马、牛、羊等动物的“去势之术”或被阉割的动物名称。)施于男性的“椓”是去掉生殖器,而用于女性“幽闭”的“椓”,却比较复杂,具体的手段,至今尚没有定论。有人认为是把女性关闭起来,有人认为是把女性生殖器缝起来;有人说是用木锥将女阴外部捣烂后待其愈合萎缩,或将耻骨敲断;还有人认为是猛击女性腹部,造成子宫下垂堵塞。鲁迅曾经自称对这种酷刑作过研究,他在《病后杂谈》里谈到这种酷刑说:“决非将她关起来,或者将它缝起来。近时好像被我查出一点大概来了,那办法的凶恶,妥当,而又合乎解剖学,真使我不得不吃惊。”
在甲骨文中,有关“豕”的文字很多。我们稍加整理解说,便可以看到一幅幅远古生活的侧面图和局部图。
说到豕字的异体,不能不提到“亥”字。《说文解字》解释亥字,除了草根、天干之外,又说它同于“豕”。还说它有“二首而六身”后世学者如郭沫若等人,也认为“亥”字就是“豕”字。但是在甲骨文以及金文中,“亥”字与“豕”字的字形字义却并不相同,因此,“亥”字是否就是“豕”字,无法确定。《吕氏春秋·察传》讲过一个故事:“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子夏是战国人,当时那个读“史记”的人也许用的大篆钞本,把“己亥”误为“三豕”,是字形相似而造成了混淆。如果古代的“亥”就是“豕”的话,子夏也许就不会说“豕与亥相近”,而应该说“此处豕应读亥”了。子夏是孔子的门徒,孔子本人重视礼器,对礼器上那些古代文字也一定有所研究,孔门弟子,是不会以“亥”为“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