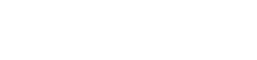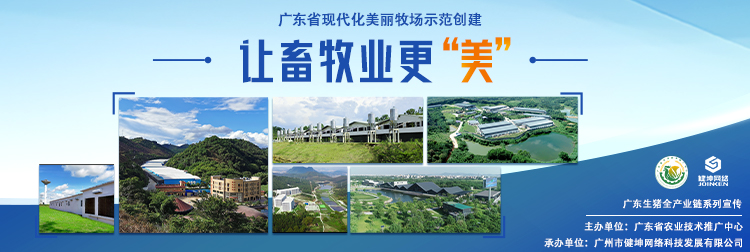考古中的猪文化
第一节 闻名中外的“玉猪龙”
早在20世纪的30年代,沉寂于地下5000多年的东北红山猪首玉器——“玉猪龙”还只在民间古董商人的手间悄悄流传,就因其奇特瑰丽的造型和艺术价值而名震中外,以至于吸引来了大批外国淘宝者。
地不爱宝,1971年,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一位农民在植树之时,挖出了一件红山玉龙。当时,这位农民认为是一块的环状的石器,顺便拿回家给小孩子当玩具。1972年的春天,赤峰市博物馆的人下乡搞文化普查,在无意之中,看到一位小孩子用绳子拉着一件半圆形的石器玩耍。博物馆的人觉得可能有价值,于是把它征集回去了。经过专家们的多次鉴定,判断为玉龙,是一件国宝。因此,喜讯不胫而走,赤峰出土了“中华第一龙”的消息轰动一时,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之后,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各地的红山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玉器。其中,猪的造型是最多的一种,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一种。
在内蒙古东部老哈河的支流英金河畔,有座暗红色花岗岩构成的山峰,叫红山。红山文化的得名,就根源于这座饮誉中外的山峰。今天所说的红山文化,是指我国东北地区的一种新石器文化,距今约5000年左右,大致分布在吉林省西北部、辽宁省西部、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及河北省北部。红山文化因其出土的猪形礼玉——玉猪龙扬名中外,加之具有酋邦社会向国家时代转型的文化特征,一直被学术界当作史前文明的典范来进行研究。
据有关资料,在辽宁建平牛河梁、喀左县东山嘴,内蒙古敖汉旗大洼乡、赤峰市巴林右旗羊场、巴林左旗那斯台,河北围场下伙房村等遗址出土有大量的猪首礼玉,即学术界一致称道的“玉猪龙”。在辽宁建平牛河梁“女神庙”遗址,还发掘出了动物像“神猪”的头、蹄等。在内蒙古敖汉旗大洼乡小山赵宝沟文化遗址,出土绘有猪、鹿、鸟形象的陶尊;在赤峰兴隆洼文化遗址,发掘出了猪首石龙。因此,屡见不鲜的猪形象引起了各界广泛的关注。
“玉猪龙”的象征意义,学术界有多种猜测,有礼器说,有图腾说,有礼器兼北斗说等。其中,冯时先生持礼器兼北斗说。在他看来,猪首为北斗的象征。尤其是出土于辽宁省凌源县的三官甸子红山文化墓地的一种双猪首三孔礼玉,它长8.9、宽2.6厘米,主体部分为三个并列的圆孔,孔径1.9厘米。并列的三孔两端各雕有一个面向外的猪首,底部有四个漏斗状的小孔。冯时先生认为,这件玉器两端的猪首是北斗的象征,玉器中央的三孔可以视为从斗魁引出的斗杓三星,位置也极为合理。冯时先生又认为,出土于辽宁牛河梁的双人首三孔玉饰也是北斗的象征,双人首是双猪首的拟人化而已。当然,在我看来,“玉猪龙”是“中”,象征着神圣的交媾,同时兼象征北斗等多种涵义。
有学者不同意把猪形礼玉命名为“玉猪龙”,譬如中国神话学会会长叶舒宪先生认为应是“玉熊龙”,并援引商代墓葬出土的“玉熊龙”为证,由此推论出“中华民族的龙图腾来源于熊”的说法。虽然有许多学者不同意叶舒宪先生的说法,但他的观点也可备为一说。
据现有的考古资料,我们认为这种玉礼器应属猪的造型。因为玉礼器的头部像野猪,呈怒目圆睁状,身体弯曲如环,某些礼玉獠牙外露,背部近头处都有一小孔。目前出土的猪形玉礼器中,最大的有15厘米,最小仅4厘米。冯时先生通过比较分析,认为玉猪龙中具有獠牙的野猪与小山陶器上绘于星图中央的生有獠牙的野猪不仅形象一脉相承,而且也具有相同的古天文学含义。天津市文化局收藏有一件非常奇特的猪形玉礼器,它仅具猪头部分,形象十分逼真,也当是北斗的象征,与红山猪形礼玉的含义完全相同。
猪形礼玉身体弯曲如环,隐藏有什么文化含义?冯时先生解释说,这可能描述了斗魁四星绕极运动的圆形轨迹,意味着环状猪形礼玉的特征造型至少有两方面的象征意义,一方面,它可能表现了极星天枢绕北极旋转而形成的中央璇玑天区,而环状部分的中央圆孔应当象征天极之所在;另外一方面,它当然也是北斗拱极运动而建时的反映。
当然,对于猪形礼玉的象征意义的破解,学术界也有不同的意见。许多学者认为猪形礼玉一种图腾崇拜的遗迹,它表明猪是红山文化先民的图腾。也有人说猪形礼玉是求雨祈望农业丰收的礼器。在东北地区的一些文化遗址中,从兴隆洼文化到红山文化,都发现有随葬猪的现象,既有家猪,也有野猪。这一现象表明,红山文化先民已开始驯化野猪,养殖家猪。据历史记载,活动于东北地区的各大古民族都擅长养猪,譬如古肃慎人等以养猪著称于世,可谓地下和文献两相印证。
从文献记载和文化人类学资料看来,猪的象征涵义也很多,譬如地母、祭雨、淫欲、交媾、凶猛勇武、财富、人等等,不一而足。因此,红山文化中的猪形礼玉的象征涵义很多,应存在多种可能性,我们不能按照今天的逻辑推理认定它一定仅只象征着某一形象。
根据文化人类学资料,猪是“淫欲”女神、地母的象征。在辽宁牛河梁“女神庙”同时存在的“女神像”、“猪头像”,应当也有这种象征意义。据《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发掘简报》,“女神庙”位于牛河梁主梁北山丘顶,地势非常高,属当地红山文化分布地点的中心区。它由两组在同一中轴线上的建筑构成,一个是多室建筑,在北部,为主体,另一个单室,在南部,是附属。两者之间相距2.5米。多室建筑南北总长18.4米,东西残存最宽6.9米,由主室、侧室和前后室组成。在主室内出土有彩绘泥塑人像的头部、肩、臂、手和乳房,以及猪像的头、蹄等。
我们往往只注意到“女神庙”中的“女神像”,而忽视了“女神庙”中并存的“猪头像”及其象征涵义的阐释。“女神像”、“猪头像”两者并存的现象表明,红山文化的先民可能不但视猪为北斗,而且还把猪当作象征“淫欲”的地母神、女性祖先神、交媾神。在甲骨文中,“家”字的初义是“庙的正室”。如果考虑到“家”字的起源以及殷商文化与红山文化的渊源关系,这个“女神庙”很可能就是“家”。 在“家”里,红山文化的先民们或举行男女集体交媾的巫术或祭祀,或举行重大事务的决策,或祭祀各种神祗。#p#分页标题#e#
如果说“女神庙”仅只是孤立的现象的话,那么内蒙古敖汉旗发现的猪首石像则更能说明这一问题。据新华社呼和浩特2003年10月24日电,内蒙古敖汉旗萨力巴乡与玛尼罕乡交界处的一个山顶上,发现有一处距今4000多前的祭祀遗址,主体范围大约15万平方米,分中心、东、南、西、北5个区,整个遗址呈不规则形,有石砌的围墙,高约 2 米,保存完好。在围墙内有 200 多个圆形石砌祭坛,最大的直径 13 米、最小的直径约 4 米。其西南侧发现了一座巨型猪首石像,高约 5 米、宽约 3 米、长约 8 米,围墙外东侧、北侧的悬崖上,还发现了 10 多块巨大的人工磨光石块。有考古学家说,内蒙古敖汉旗发现的猪首石像是当时的先民祭祀的祖先神。
考古学家在“女神庙”附近牛河梁主梁顶南端斜坡上发现有“积石冢”墓葬群,并在其中一座墓葬中发掘出两件猪形礼玉。据《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发掘简报》,“积石冢”M4墓葬墓口长1.98、宽0.4—0.55、墓底长1.7、宽0.25—0.39、深0.6米。墓主头部朝东,仰身直肢葬,两腿膝部交叉,左腿在上,右腿在下。墓中随葬三件玉器,一件玉箍形礼器横枕在头部下,两件猪形礼玉首部向外并排倒置于胸前。冯时先生据此说,墓主的葬式使人不禁想起古文字的“交”字。《说文》交部说,“交,交胫也。”墓主呈交胫之形或许暗寓天地交泰之意。在《周易·泰卦》的《彖传》和《象传》中,“泰”就是“天地交”。唐代的孔颖达解释说:“此由天地气交而生养万物。”冯时先生断定墓主应为巫师的首领一类人物,而摆放胸前的猪形礼玉则是他交通天地的道具。因此,巫师的首领所有具有的掌握天极及北斗而敬授人时的职能,与其胸前摆放的猪形礼玉象征北斗及天极的含义若合符节。而我却认为,两猪首玉礼器和两腿膝部的“交”形都是两性交媾而通天地的隐喻。
根据苏秉琦先生的说法,牛河梁遗址所代表的社会“高于”一般的氏族、部落,有“凌驾”在氏族、部落之上的社会组织形式。因此,它属“古国” 形态,是一种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而据谢维扬先生研究,牛河梁遗址代表的社会可以认为属于酋邦类型,是前国家社会的一个例证。
从“女神庙”中所出的泥塑群像的内容看,似乎红山文化社会已有了等级性的秩序、社会规范的存在,以及相应的宗教观念。据《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发掘简报》说:“这些形象有的可能象征当时社会上的权势者,有的或许是受到崇拜的祖先。根据群像之间大小和体态的差别判断,似已形成了有中心、有层次的‘神统’。” 虽然还不能判定在“家”(“女神庙”)的神统中有无“至上神”——“上帝”,但我们至少可看到有一个中心的大神——女神存在。她是凶猛勇武的猪神、战神,可能还是显赫的女性祖先神。在远古先民看来,北斗就是天的“中心”或“中央”。如果要说到猪形礼玉、“女神庙”中女神像、猪头像是北斗的象征的话,那么猪神确实是一个“中心”或“中央”。拙作《释“中”》认为,“中”(或中央)的本义是神圣的交媾,是文化和生命的来源。从原始宗教上讲,猪首礼玉也就意味着是“中”——神圣的交媾,至上权力的象征,所以它被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先民中的首领类人物独占。从生殖崇拜信仰上讲,“猪的传人”——红山文化的先民惟有通过猪首礼玉才能确认自身生命的意义与价值。
第二节 良渚猪形神徽的解读
北有红山文化“玉猪龙”,南有良渚文化神人猪面“神徽”。在今天看来,可谓是争奇斗艳。不过,在远古时代,它们仅只是满天星斗似的文明起源地中的两点而已。
良渚文化是分布于太湖流域一带的一种新石器文化。它是由马家浜崧泽文化类型晚期发展来的,以随葬玉器数量和品种之繁多闻名中外,也是史前文明的典范,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之一。它的时间断代大约在公元前3300—前2200年左右。
在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礼玉中,各种礼器上的“神人兽面”纹饰最为引人注目。关于它究竟像什么?也有多种说法。赵国华先生说它像男根,是男性生殖器崇拜。俞伟超先生说它像女神彰露着獠牙阴户,但未见论文刊布。萧兵先生说它是女神、女阴、野猪的兼体造型。冯时先生则说它是用以象征北斗的猪。而我却认为,它应当是“中”——神圣的交媾之象征,则采萧兵先生和冯时先生的观点自然包括在其中,并且更能阐述“神人兽面”纹饰的原始意义。
我们知道,在马家浜崧泽文化中,早已出现猪形器物和雕刻有猪图像的陶器。作为继承了马家浜崧泽文化的良渚文化,猪的形象则是处处皆有。据邓淑苹《蓝田山房藏玉百选》收录的良渚文化的一块玉璧礼器,我们明显看到了其上绘刻的猪形头像。玉璧为台湾许作立先生所藏,灰黄色。外径15.6、孔径4.6、厚1.25厘米。该猪形图像镌刻于璧面的中央,猪口微张,背有鬃鬣,长尾上扬,有一后腿系有绳索。图像长4.8厘米。冯时先生说,该猪形图像上刻的四个星饰,当是以猪应合斗魁四星的象征,而微扬的猪尾虽然显得过于夸张,但却像是连接斗魁四星的斗杓,因此在形象上与北斗十分接近。
在冯时先生看来,良渚文化的玉礼器及相关器物上的猪形图案十分普遍,甚至于可以说没有任何一种图案可与之相匹。浙江省余杭县反山良渚文化墓地出土的乙型玉琮绘制的猪首图像当是迄今所见这类图像中最逼真的一种。通过比较发现,大部分玉琮所雕刻的图像一致,只稍微略有一些繁简的变化而已。
据说,其中最为引人入胜的典型图案还是反山M12:98玉琮“神人兽面”纹饰,它是一直学术界讨论的重点对象。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对在发掘简报中的描述:
纹装区之一是四个正面的直槽内上下各有一个神人与兽面复合像,共八个。直槽内雕刻纹饰尚属首见。八个纹饰内容基本相同,但雕刻深度、大小有些微差异。神人的脸面作划鼻翼。阔嘴,内以横长线再加直短线分割,表示牙齿。头上所戴,外层是高耸宽大的冠,冠上刻十余组单线和双线组合的放射状羽毛,可称为羽冠;内层为帽,刻十余组紧密的卷云纹。脸面和冠帽均是微凸的线浮雕。上肢形态为耸肩,平臂、弯肘、五指平张叉向腰部。下肢作蹲踞状,脚为三爪的鸟足。四肢均是阴纹线刻,肢体上密布卷云纹、短直线和弧线,关节部位均有小尖角外伸。在神人的胸腹部以浅浮雕突出威严的兽面纹。重圈为眼,外圈如蛋形,表示眼眶和眼脸,刻满卷云纹和长短弧线。眼眶之间有短桥相连,也刻卷云纹和短直线。宽鼻,鼻翼外张。阔嘴,嘴中间以小三角表示牙齿,两侧外伸两对獠牙,里侧獠牙向上,外侧獠牙向下。鼻、嘴范围内均以卷云纹和弧线、直线填满空档。整个纹饰高约3厘米、宽约4厘米,肉眼极难看清细部。这神人兽面复合像应是良渚人崇拜的“神徽”。#p#分页标题#e#
纹装区之二是以转角为中轴线向两侧展开的简化“神徽”。四角相同,左右对称。以三道凹槽将一个凸面分成相等的四节。第一节和第三节的上端各有细弦纹,以六根细弦纹为一组,两组弦纹之间雕刻纤细的连续卷云纹,这应是神人所戴冠帽的变体。所以四节实为两组,上下两组相同,与正面直槽上的图像对应一致。变体冠帽下为神人的脸部,重圈为眼,小尖角为眼角,鼻子省去,阔嘴,嘴内填满卷云纹、弧线、短直线。凹槽下方一节雕刻兽面纹,与直槽内的兽面纹相似,但也无鼻。兽面纹两侧个雕刻一鸟纹,鸟的头、翼、身均变化夸张,刻满卷云纹、弧纹等,可称“神鸟”。这一组神人与兽面复合像,基本格局与直槽内的“神徽”一致,省去了神人的四肢,冠帽作了变形,面部略有简化,增加了一对“神鸟”。这种以转角为中轴线向两侧展开的简化“神徽”,是良渚玉琮纹饰的基本特征。
冯时先生认为,这种神人兽面图案,是猪首图像与一种倒梯形的斗魁图案的合体,与前揭反山乙型玉琮绘刻的猪首图像一致,是北斗或北极的象征。迄今为止,良渚文化出土的各种玉礼器中,凡是绘刻有类似神人兽面“神徽”图案的,虽然或稍有差异,但其猪首图像渊源是一致的。冯时先生说,这种猪首图像很奇特,几乎总是与一种倒梯形的斗魁图案合刻在一起,它们或者作为一种带有斗魁形脸的神徽图像的一部分,或者在猪首之上或天盖璇玑之下雕绘出一个斗魁形象,或者索性绘刻于制成斗魁形状的玉冠饰之上,很有可能,斗魁图案与猪首图像具有相互阐释的独特作用。
萧兵先生则说,良渚文化中神人兽面的“神徽”可能是女神、阴户、野猪的“兼体造型”。“神人”和“兽面”整体统一,相互阐释,不可分开。神人即大母神,兽乃是野猪。神人的乳房恰恰兼为兽的双眼,兽鼻掩盖肚脐,野猪獠牙嘴则是女神的阴户。在《山海经》中,刑天就是一个以乳为眼、以脐为口的神人形象。根据文化人类学资料,女阴以“兽口”的形象出现屡见不鲜。因此,萧兵先生说:“联系到良渚文化‘神人兽面’,必须克服一个巨大的心理障碍:如此崇高伟大的良渚文化宗神(专家们的称呼,有‘族神’、‘祖先’、‘图腾神’、‘巫神’直到‘至上神’,唯独回避了可能最大的‘母神’),居然毫无礼貌地炫耀着她的生殖或繁育的器官,而且面目狰狞,形相丑陋。然而,良渚仍处‘原始’社会,其崇高感、羞耻心,审美价值与标准,跟近现代迥乎相异,甚至相反。真善美都是历史范畴。那时炫耀生殖器官,不但毫无淫猥之‘故意’,而且是庄严端肃的行为。母亲、母性、母神决定着人类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关系着社会的‘生死存亡’,漠视或侵犯‘玄牝’,就会导致种群的衰减直到灭亡。”
萧兵先生的解释非常有理,在远古时代,社会普遍信仰生殖崇拜,先民的崇高感、羞耻心、审美价值与标准,以及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完全与现代人不同。似乎许多观念都是一个反动,今天的人们以“淫”为万恶之首,而远古时代的先民却以“淫”为尽善尽美之先。远古时代的先民不但公开集体行“淫”,而且还认为男女交媾是一种通天地的巫术,为一种极为神圣、庄严端肃和崇高的祭祀仪式。
古代野猪的传统造型正面观是獠牙突出,“截鼻”,两眼孔齐整圆大。萧兵先生据此判断,良渚文化神人兽面“神徽”中的兽面当为野猪,而不是某些学者所说的“龙”、“虎”、“鸟”等动物,并且神人与野猪对立统一,可以互指兼喻。
原始社会的“道德风尚”与现代完全不同,甚至于根本相反,譬如在男女两性方面。“豕”、“德”的古读相近,两字能够通训。在远古时代,“德”的内涵与周秦以下的完全不同,它更多地是被赋予了“淫欲”的内容。在红山文化、良渚文化时代的社会,先民如果像猪一样性欲旺盛、繁殖力极强、凶猛勇武,一定会被认为是有“德”之人,因而倍受社会普遍的推崇。
在中国古代,存在着人猪互喻的现象,譬如把猪称为“乌将军”、“黑面郎”、“黑相公”、“亥日人君”等,又将女人称作“猪婆子”,把男人称为“脚猪子”(种猪、公猪)。有证据表明,人猪互喻,还表现为“家”、“冢”互指兼喻。在堪舆学中,风水结穴的位置类似于“女阴”交媾区。也就是说,活人、死人同住在喻象为“女阴”的“穴场”之中。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喻象为“女阴”的风水“穴场”相当于良渚文化神人兽面“神徽”的“獠牙阴户”。
在文献记载中,食欲与性欲可以互指兼喻。古人往往将性欲旺盛的人比喻成艾猳或娄猪,则把食欲贪婪的人比喻成封豕,猪八戒正是这两者结合在一起的典型形象。而在今天,猪是性欲、食欲旺盛的象征,几乎是人人皆知的常识了。
远古时代,性欲的大小或者生殖力的大小是衡量一个部落首领的是否有“德”的神圣准绳之一。一个部落首领地位的“合法性”与否在于其是否像猪。赞美一个部落首领善“淫”像猪,也就是称颂他有足够充分的繁殖力,能够确保他所领导的社会共同体繁荣昌盛。如果一个部落首领无“德”,其则会被全民无情地驱逐。拙著《生殖崇拜与中国青铜时代》曾认为,远古时代的人力可能是每一个种族最大的需求,凡是像猪一样繁衍出成群子孙的人,均被视为有“德”有“功”于种族之人。
在古代文献中,“德”可训作“生”,“生”就是“性”,为神圣的两性交媾。《管子·心术》:“化育万物,谓之德。”《易·系辞传》:“天地之大德曰生。”贾谊《新书·道德说》:“所得以生,谓之德。”根据古文字学,“德”能释为“植”,植、殖相通,都是两性的交媾而繁衍生命的意思。#p#分页标题#e#
在远古时代,“色”是“德”的最初内涵之一,因此“德”还可以解释成“色”。《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有“女德无极,妇怨无终”,《史记·晋世家》有“子不疾反国,报劳臣,而怀女德,窃以为子羞之”。所谓“女德”就是“女色”。可见,古人视两性交媾是一种有德的象征。
正是如此,部落的领袖人物往往都是“交媾大师”。据说黄帝就是交媾大师,“御” 了一千二百个女性,不但最终做了神仙,并且蔚然成为华夏族的祖先。
熟悉自古以来的“文化传统”后,那么就能很好理解中国人为什么把女人称“猪婆子”、把男人称作“脚猪子”的原因。看看“家”字、“冢”字就可知道,古人对“猪”的崇拜与信仰是异常的狂热。
秦始皇巡狩会稽,刻石明令:“禁止淫佚,男女洁诚。夫为寄貑,杀之无罪”。 可见,在浙江会稽山一带,人们就把与众多女人通淫的男人比喻为来回走动的“脚猪”。
良渚文化神人兽面“神徽”的象征意义可能很多,它可能同时象征多种含义,譬如交媾、北斗、中央、祖先、雨水、地母、勇武、丰饶等等。萧兵先生说;“金文族徽有‘人’胯下为‘豕’之意象,或隶定为‘■’(上大下豕),跟良渚‘神人兽面’复合结构趋同。古埃及大母神伊西斯(Isis),举腿张牝,座下的野猪暗喻其阴门具有强大而无法控驭的魔力;佛教摩利支天胯下的野猪本亦此意。这些都可以讨论时加以考虑。”萧兵先生的意见极具启发意义,古代有“骑猪”、“骑豕”的词汇,一般说指的是吓得屎尿拉在裤裆。很有可能,“骑猪”、“骑豕”的初义是指孕妇生产,以此象征交媾和繁殖。
因此,在我看来,良渚文化神人兽面“神徽”与红山文化的猪形礼器的象征意义大同小异,都是“中”——神圣的交媾。它们还意味着当时的先民确认自己是“猪的传人”,深信生命和文化的的根本在于野猪。它们的拥有者,大多是部落的“中心”人物——首领或巫师长,既是权力的象征,也是权力“合法”、有“德”的根源。
第三节 猪在史前文化中的象征意义
如果说要阐述“猪的传人”信仰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据文化人类学资料,在史前文化中,猪可能是女性、地母、交媾、北斗、中央、勇武、雨水等的象征,甚至于还可能是部落首领权力的标志,巫师交通天地的一种媒介。
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社会普遍流行葬猪的习俗。《山海经》记载有瘗埋猪肉的祭仪。《山海经·北山经》:“其祠之毛,用一雄鸡彘瘗。”可谓文献与地下考古能相印证。
户晓辉认为,猪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它曾经是地母的动物化身和象征物,当时的人们用猪作随葬品,实际上是借助猪或地母的繁殖力与生命力使死者复活的一种巫术手段。户晓辉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新石器时代的先民认为,“中”——神圣的交媾是永不死亡的一种巫术手段。猪象征着神圣的交媾,以它随葬,应存在祈求不死或复活的可能。不过在我看来,葬猪的宗教目的还存在多种可能。那个时代的先民们认同自己是“猪的传人”,相信人从猪世界来,仍得回到猪世界去。因而可以这样说,史前文化的先民们还可能把猪当作回归“祖先世界”的一种媒介或象征。
起源于新石器时代的葬猪的习俗延续了几千年之久,许多人都把葬猪当作一种财富的象征,并几乎成为常识了。然而,葬猪象征财富一说是难以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譬如汉代的流行随葬握猪,目前出土有石握猪、玉握猪,如果说玉握猪能象征财富,我们却无法把石握猪以及木猪也当作一种财富的象征。因此,葬猪习俗更主要是一种宗教信仰,不然的话,难以延续几千年之久而不衰。
猪类的起源历史很悠久,而人类却相反,还非常年轻。大概在4000万年前,猪就已出现在地球上。2000万年前左右,猪科动物已经在欧洲、亚洲和非洲广泛分布。有人说,全球有七个地点同时驯化野猪。人类开始把野猪驯化成为家猪,有 10000年左右的历史。可以说,猪类是人类出现和成长的见证者之一。自古以来,野猪既是人类的天敌,又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肉食来源之一。
在史前时期,野猪遍及中国各地,包括台湾省。野猪因觅食、拱土和搏斗的需要,嘴长,头部大而伸直,头部的比例占体长的三分之一甚至更长;由于时刻面临险恶的生存环境,反应敏捷,性格凶猛;毛色偏暗,以利隐蔽保护;四腿长而瘦,擅长奔突。野猪十分凶猛勇武,难以驯化,性格暴烈,繁殖力旺盛。于是乎,野猪成了先民崇拜的对象,并被认为是生殖宗祖神。
根据到目前为止所知的资料,中国距今大约10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主要有湖南省道县玉蟾岩遗址、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吊桶环遗址和河北省徐水县南庄头遗址等数处。四处遗址中都出土有猪类遗骸,但我们还是无法确证其究竟属野猪还是为家猪。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出土有新石器时代的猪牙和颌骨,个体数为67个,其中65%为2岁以下。有说是距今10000—7000年之间,有说距今5000年左右,有说距今9000年左右,等等,加上既没有测量猪臼齿的长度和宽度,也没有研究牙齿磨蚀状况和猪的年龄的关系,因此我们难以判断其究竟为野猪还是家猪。
目前考古学界公认的所知最早的家猪,出自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距今8000年左右。有人说,中国新石器时代里家猪的出现至少要比栽培农作物和制作陶器晚2000年左右。这些都是一种猜测,仍然有待于将来的考古发现。
据有关资料,中国各地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兽畜骨骼和模型中,以猪的数量最多,占三分之一左右,在一些晚期遗址中出土的猪骨数量更大。尤其是随葬猪下颚骨的现象,几乎遍及各个史前文化古遗址。在甘肃永靖大何庄齐家文化遗址中,发现12座墓随葬了36块猪下颚骨。在同一地区的秦魏家遗址中,138座墓中有46座随葬猪下颚骨,达430块,数量十分惊人。山东胶县二里河遗址,在66座大汶口文化墓中,随葬有猪下颚骨143块。而在大汶口遗址,在138座墓中,随葬猪下颚骨96块。随葬猪牙、猪颚骨乃至整头猪的习俗遍及各地,分布范围广,延续时间长,可算是中国新石器时代一种非常流行的葬俗。#p#分页标题#e#
当然,葬猪风俗的流行也表明当时的养猪业十分发达,并意味着猪可能还是一种可供交换的活动财富。有文化人类学证据表明,某些民族流行着将猪下颚骨当作家庭富有的标志的习俗,譬如生活在在西藏珞渝马尼岗一带的珞巴族博嘎尔部落即是如此。虽然猪是财富的象征,但并不意味着葬猪的目的就在于死者显示财富,而应为出于宗教信仰的需求。
因此,史前文化中随葬猪的典型而普遍的习俗,可能是借助象征着“中”——神圣交媾的猪使死者复活或不死的一种巫术手段,也可能是希望通过“中”回归“祖先世界”,更有可能还兼具有多种象征意义。如果说史前先民葬猪习俗之目的有可能为回到“祖先世界”去的话,那么他们则视猪为“祖先”,是生命和文化的来源。或者说,他们认为自己是“猪的传人”,希望通过猪来确认自身的价值与意义。
第四节 汉魏六朝葬猪习俗
史前文化中的葬猪习俗,一直延续到文明时代。夏、商、周三代不说,汉代人也非常爱猪,各地屡屡出土有各式陶猪和陶猪圈。譬如汉景帝阳陵还出土有陶猪大阵,更是惊人,每只小乳猪通长0.16米,高0.06米,分黑白两色,竖耳、长嘴、尾或卷或直,形象逼真。
在汉代,除随葬陶猪外,社会上还流行随葬石猪、玉猪,即将玉、石雕琢成卧猪形,握放死者手中,两手各一个,在丧葬礼仪中称“握”,也称作“握猪”或“握豚”等。握猪葬俗在汉魏六朝盛极一时,延续于唐宋,波及于元明,只是日渐衰微而已。
握猪中使用玉制成的,又称作“玉豚”,因在汉代最为兴盛,所以也叫做“汉玉猪”。“汉玉猪”中有包金玉猪,其雕刻技法极为精细,被称作“汉八刀”。从出土的“握猪”的形态分析,西汉握猪刀法抽象简单,多数都呈圆柱形,底面为平面,圆柱的一端稍细,以一面坡阴线界出猪头。猪头上以阴线雕枣核形眼,圆柱两侧又以一面坡阴线雕出四肢轮廓,四肢呈卧形,在接近于器底部之处略作切削,圆柱另一端的上部略圆,为猪臀,臀中部尾根处有一小凸榫。东汉握猪形象逼真,雕出四腿成卧猪状。魏晋六朝则形象似野猪,形态上较汉代玉猪复杂,颈部细于头身,头上有锯齿形的鬣,四肢短小,分别伸向前后,呈奔跑状态。唐宋之后又变回汉代形象。唐元和之后,又流行随葬铁猪。
可能是因为人们相互攀比,奢侈之风愈演愈烈,握猪越来越奢华,其造价越来越高,所以有人提倡节俭,主张“改革”“习俗”。六朝颜之推就告诫后代,崇尚简朴,不必随葬玉豚之类,《颜氏家训·终制篇》说:“至如蜡弩牙、玉豚、锡人之属,并须停省。”
有人说,猪是财富的象征,葬猪意味着死者将在另外的世界可享用财富。这种说法看似合乎道理,但却很难成立。如果葬猪习俗背后没有一种宗教信仰作为支撑,是很难以延续数千年时间之久的。在我看来,葬猪无非在于通过猪的获得某种宗教或文化目的。猪是“中”的象征,意味着神圣的交媾,或能升仙,或能回到祖先世界,或能不死、复活,或能荫庇后代,等等。前已述及,生、死同“穴”,所以“家”、“冢”不分。“猪的传人”不管是生是死,都得作为“猪的传人”而“活”着。因为猪象征着神圣的交媾,所以只有通过随葬它才能达到“祖先世界”或神仙世界,以及完成人间的种种世俗目的。
注释:
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第111页。
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第111页。
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第112页。
辽宁省文物考古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8期。
辽宁省文物考古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8期。
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第112页。
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0页。
辽宁省文物考古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8期。
赵国华,《生殖崇拜与中国青铜时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98—322页。
萧兵:《良渚文化“神人兽面”的兼体造型和意蕴》,《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6期。
萧兵:《良渚文化“神人兽面”的兼体造型和意蕴》,《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6期。
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第113—121页。
邓淑苹:《蓝田山房藏玉百选》,年喜文教基金会,1995年。
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第115页。
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第115页。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对:《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
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第115页。
萧兵:《良渚文化“神人兽面”的兼体造型和意蕴》,《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6期。
萧兵:《良渚文化“神人兽面”的兼体造型和意蕴》,《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6期。
萧兵:《良渚文化“神人兽面”的兼体造型和意蕴》,《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6期。
户晓辉:《猪在史前文化中的象征意义》,《中原文物》,2003年第1期。
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图录》,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444页。